|
你无法把一个女人和战争联系在一起,因为女人往往是被动地承受战争的苦难或泪水。在王玉清的内心深处,她并不因为享受了军阀的财产而背负罪孽,她只是一个普通的旧时代女人而已。 有人问她:"你觉得解放前你跟刘文彩生活的12年,是否幸福?"她答:"咋个不幸福嘛,过'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寄生虫'生活!"或许提问的人另有深意,可在王玉清这里,那段日子确实有滋有味。 家境一般,颜值突出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王玉清同年出生在成都大邑蔡场万延村。她的父亲是一个街市上卖糖的坐商,养着五口人,足够度日而已。 在动荡不安的社会局势中,这样的人家,轻而易举的会成为战争的微不足道的背景,本来王玉清或许也准备迎接这样的命运。 但家境一般的她,偏偏长得十分出众,是远近闻名的一枝花。或许这就是"天生丽质难自弃",被当时大军阀刘文辉的哥哥刘文彩看中,一九三七年,当时二十五岁的王玉清嫁给了五十二岁的刘文彩。 关于这门亲事,大家众说纷纭。有人说王玉清是刘文彩偶然看见,后通过某种方式"霸占"的。 但后来记者采访已经八十多岁的王玉清时,她对这种说法感到很气愤,瞪大眼睛辩解道:"我是明媒正娶的!" 可以想见,一九三七年那个清晨,望着红色的轿子前来接她,在灰瓦房的胡同里穿梭的时候,她是有多么开心。在她的生命中,从此开始了一段幸福的旅程。 碍于面子,并不隆重 刘文彩何许人也?在当时四川人民的记忆中,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恶霸。靠着弟弟刘文辉大军阀的身份,成为川南最大的税务官。 为了给弟弟筹集军费,苛捐杂税,巧设税款名目,而且还预支几十年的税款,弄得人民苦不堪言。 天府之土,沃野千里,连日本人都鞭长莫及,却使得刘文彩和其代表的军阀系好好的当了几十年的土皇帝,为了自己的利益,玩弄底层人民于股掌之中。 即便是这样的人,在五十二岁高龄的时候明媒正娶一个小女子,自己的第五个姨太太,竟然也觉得面子上有些挂不住。 虽然请了轿子去接,但并不隆重,只办了几桌酒席,邀请了当地的一些商贾官吏。刘文彩拿起主宗牌位前的铁杵,在锓上稍微敲一下,就算是给了王玉清一个堂堂正正的地位了。 面对佳人,不能自己 不论是多高的权势,也不过这一具躯体。不论其所作所为会影响多少人的生活,以至于连带影响到他们的感情,其个人毕竟还是只关心自己的喜怒哀乐。 王玉清的确是佳人,而且本身温柔贤惠,活脱一个邻家闺秀,虽然并不隆重的娶过来,但却赢得了刘文彩的一份心。 在婚后,刘云彩对她百般宠爱,金银珠宝、绫罗绸缎自然不在话下。而且经常性的,刘云彩在四处作公开的出席时,身边也常带着她。 她通常踩着一双高跟鞋(因为其身高不高),安静地站在刘云彩的旁边。在上流阶级看来,这是华贵而上等的模样。 对于王玉清的要求,刘云彩也毫不含糊。为解决王玉清晕车的毛病,刘在一九四六年花费两千多法币,专为她购进一辆美式吉普,供她出远门时享用。 每次王玉清生日,刘云彩也必大办特办,张罗十几桌酒席。而其他姨太太或者情人却没有这个待遇。在王玉清的老家,也建起了大瓦房,收购了大片田地,使王家一跃而为大地主。 全国解放,地主遭殃 一九四九年,刘文彩去世,作为旧时代的丑恶而消亡了,但王玉清依旧作为旧时代的产物留了下来。 在生前,刘文彩对王玉清说:"我死后,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了!"但刘文彩死后,王玉清也并不受到他的亡灵的庇佑。毕竟解放之后,哪容得下旧军阀的亡灵作祟? 作为四川恶贯满盈的军阀,大地主,刘氏家族遭到了土改等政策的的全部洗牌。虽然刘文彩的哥哥刘文辉功大于过,于解放四川有功,被授予荣誉。 但顺应最广大人民群众和党的意志,王玉清作为地主姨太太,自然被剥夺了身份地位。 作为权力的附庸,在人民权力觉醒之际,王玉清回归为了一个普通的妇人。从此之后,她在成都一处叫"慈惠堂"的地方住了下来,靠打布鞋,做咸菜、臭豆腐为生。 这一做就是五年。好在是贫苦人家出身,在稳定的社会下,王玉清倒也过得安稳。 历经坎坷,终到晚年 后来她又结过婚,但老伴又死掉了。而且在动乱的日子里,因为以前的身份,不知受了多少批评。 不过她终于还是活着,又迎来了曙光。改革开放后,政府把这个无儿无女,孑然一身的老奶奶划作"五保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她每年有六斤菜油,四百斤口粮,四百块钱。 一九九九年的三月的一天,记者来到王玉清住的地方,这时她已经八十七岁了。 在安仁镇引路者招呼下,一个正坐在街边晒着太阳的耄耋妇人,在另一位老妇人的搀扶下,起身向他们蹒跚走来。 她一米五米略多的个子,深度驼背,满头灰发和一脸皱褶,刻下无情岁月;一双可能因患有眼疾而显得有些红肿的眼睛隐露著警惕和审视的目光,一身铁灰色布衣洗得泛白,手里还握著一根权作拐杖的木棒。 她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生活着的人,一个抛却那些纷纷扰扰,安度着每一分每一秒的老人。虽然这老人显得那么衰老,那么不起眼,不再在人世露出她的形状了。 她显得很自如,回答问题十分得体,早已经适应了语言中的生存,对于自己"寄生虫"的身份显然已经有明确认识。 然而她的内心,却依然坚持着那段她说了不知多少遍的话:"我一个妇道人家,对刘文彩外面的事不了解。我只是站在妻子的角度觉得,刘文彩这个人的性情很好。我这一辈子除了父母爱我外,就是刘文彩爱我了,再也没有第四个人真正爱过我。"于是她每天早晚各烧一炷香,给她的"老头子"烧去。 她依旧爱着她所爱的人,爱着爱她的人。爱着她的父母,丈夫,以及一切已经作为粉尘消逝在这大千世界的事物。 面对这样一个单纯的女人,偏见或许是多余的。 香奈儿包包 https://www.sumipvc.com/product/chane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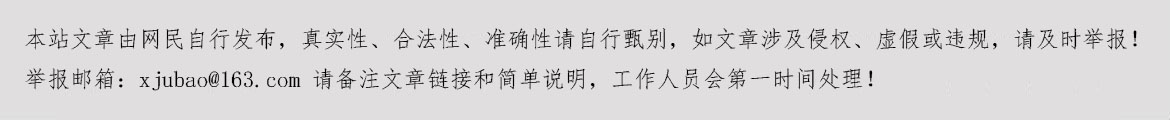
|
|
1
 鲜花 |
1
 握手 |
 雷人 |
 路过 |
 鸡蛋 |

业界动态|讷河百事通

2025-09-17

2025-09-17

2025-09-17

2025-09-17

2025-09-17

请发表评论